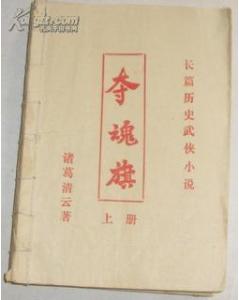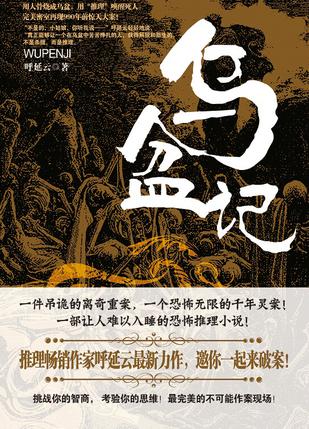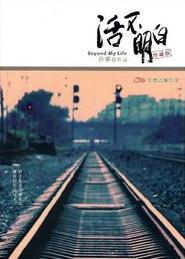当湖十局
2016-07-25 阅读 : 次
卷一:素景流年
日头晒,汗哒哒,叶儿绿,绿油油。
碧树下,一个六七岁的小男童,攥着几粒小石子,垂头对着面前泥土画的棋盘,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想的入神了,小脖子上汗涔涔的,也不见伸手擦一下。远处立着几个端着茶水毛巾的下人,因暑气都躲在了亭子里,只忧心地瞧着却不敢打扰。
笑话,小少爷下棋时,谁敢打扰那就是找死。
“这里很热。”忽然,一个软软的声音从身侧打断他。
“去去去,用你说?”小男童撅嘴看了身侧一眼,才发现蹲在他身侧的也是个小孩。不过,不同于他自己挂着汗和草泥的青色小褂子,面前这瘦弱的小男孩很干净,穿着雪白的小褂子,连小小的黑靴上都没有沾草叶。
白衣男孩柔柔笑了下:“我还以为你睡着了,怕你中暑。”
坐在树下的人哼了声,继续低头看棋。
“你可以在此处破眼。”那小男孩又软软地说了句,细长小巧的手指堪堪点着一处。
坐着的人斜眼看他,啧了声道:“你也懂?”
白衣男孩点点头,笑出了两个梨涡。
小少爷撇嘴看了他会儿,拍了拍身侧:“兄台,请坐。”
那干净的小男孩摇了摇头,温温地道:“我不坐了。”
小少爷看了眼他的褂子,心知他是怕坐脏了,想了想,对着远处的下人道:“顺儿,把你外衣脱下来。”
远处下人听这一声吩咐,显然愣了下,心道少爷何时这么体恤下人了?怕我中暑?他没敢再多想,利索地脱下来,快跑上前,躬身道:“屏少爷。”
小西屏拍了拍地面:“搁这儿。”
顺儿愣了下,见他晶亮的眼睛眯起来,微一哆嗦,赶紧铺好:“屏少爷还有什么吩咐?”小西屏看那小男孩也流了些汗,想了想又道:“那些凉茶来。”
顺儿哎了一声,溜烟儿地跑走,不一会儿就端了杯茶来。
青瓷的杯,盖拿走了,凉茶上还飘着夏花。
“兄台,请。”小西屏有模有样,两手捧着茶杯,嫩呼呼的小脸上尽是客套。
白衣男孩愣了下,软软笑着,接过茶喝了小半口,又递回给他:“你也喝,免得中暑。”
小西屏抽了抽眉心,将茶杯转了半圈,当真就喝了口。
顺儿看着俩小孩的动作,嘴巴张了张,没敢出声。屏少爷的洁癖当是众所周知的,连夫人的脸面都不给…
…不过这干净小孩还挺有本事,都一个时辰了少爷都没喝过水。
喝了人家的水,又有衣服垫着,白衣男孩也不好再说什么,就势坐了下来。两个小孩就这么探讨起棋面来。
小西屏就是仗着小聪明,基本功不大扎实,听着面前男孩一板一眼地讲解着封,断,破眼,不觉听进了心里。比起父亲大人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讲解,这个男孩说的简单了不少,又因那软软的嗓音,在这燥热的夏也让人心里凉滋滋的,两个字,舒坦。
不过,小西屏偶尔的话,也令那白衣男孩颇为惊异,不套常理,剑走偏锋,完全不同于他自己平日所学。
二人将青草地上的棋盘摆满时,都长出了口气。
小西屏眯眯眼,仰头直接躺到草地上,头刚好伸出到树荫外,被太阳晒得彻底闭了眼。明日就要拜师了,那俞老头也不知道什么套路。他被晒得困意渐浓,只隐隐觉得要是旁边这小兄台做老师也不错……
待一个时辰后,他才迷迷糊糊醒了,看身边已没了人。几个下人立在一侧为他挡着日头,顺儿放大的笑脸就在眼前:“屏少爷,您醒了?”
小西屏啊了声,一下子蹿起来,看了看四周:“那小子呢?”
“您说施家小少爷?”顺儿忙捡起自己褂子套上。
“施家小少爷?”小西屏脑中闪过一个念头,嘴巴张得能装鸽子蛋。
“可不是,”顺儿替他捡着褂子上的碎草,“要不是施家小少爷,小的怎么敢放人过来。”
“施襄夏?!”
“是啊——”
小西屏砰地坐回了地上,猛地咬住下唇,露出一排未换全的乳牙。
栽了栽了,这就是爹不分白日黑夜用来踩自己的……海宁神童……
“屏小爷?”顺儿吓了一跳,不敢碰他。
“顺儿……”小西屏水汪汪的眼睛里,都是悔意,“爷这回栽了……”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卷二:青梅竹马
当湖书院门口,坐着一少一童。
“顺儿,你说这又不是魏晋,”小西屏热的眼前直泛白光,“书院也就是个派头,听着过瘾,怎么这不开化的老头就不让本少爷进门呢……”
他汗流到了下巴上,拍了拍顺儿,顺儿忙不迭地摸出汗巾,替他仔仔细细擦了,没敢答话。人家说是晨起入书院,少爷这一觉都到午膳了,也难怪书院的先生有气,不过好在是少爷,坐一坐也就进去了。
只是这天……实在热了些。
夏蝉叫的让人躁得慌,小西屏实在闲来无事,拿着个尖石头开始画棋盘,刚没划几下就被个影子遮住了,抬头看去,背着光的一张脸上尽是软绵绵的笑:“你怎么不进去?”小西平从眉心抽抽到太阳穴,想凶凶不出,想笑又憋屈,只吊着嘴角哼了声。
小襄夏依旧是身小白褂子,脖上戴着亮晃晃的赤金丹凤颈圈,看得小西屏又是一阵烦躁,站起身拍拍屁股,张口要说什么时,小襄夏身后的下人已跨前一步,怒气冲冲地盯着他:“我家少爷和你说话,是你的福气,你个奴才竟敢不答话!”
小西屏傻了,怔怔看着这个陌生人,顺儿却像被人咬了一样,忽地一下站起来,立刻高出那人半个头,阴森森地俯视他道:“我家少爷正心气不顺,赶紧给我滚。”
那人倒也不惧,立刻瞪了回去。
于是当湖书院前,傻站着两个小童,还有两个怒目而视的少年,立刻引来了不少路人围观。
“如意,”小襄夏温温地道,“不得无礼。”
他声音虽软,却不乏威严,如意忙低着头退了几步。
小西屏见此,也赶紧彰显了自己的大度,挥了挥手道:“顺儿,给施家小少爷让道儿。”顺儿啊了声,见他挑着杏眼看自己,也赶忙让开了路。
“兄台,请。”小西屏抱起拳头,施施然一礼。
“你怎么不进去?”
小西屏闷了下,舔了舔嘴唇,道:“晚到了,先生不让进。”
他说完,小襄夏身后的如意‘切’了声,被小襄夏淡淡看了一眼,立刻噎住了。小襄夏回过头,温看了眼面前青褂子的小西屏,轻叹了口气:“你等等,我去和先生说说。”小西屏啊了声,刚要说不用,他已经提步进了书院大门。
不过一会儿,就有人请了二人进去。
小西屏正正经经地拜了师,才知道这山阴俞长
侯只收了四个徒弟,而自己和施襄夏就是其中之二。
因二人年纪相仿,便被先生安排对弈练手,日日练夜夜练,睡前练睡醒练,练得昏天昏地。可惜一年后,小西屏依旧胜不过这个软软笑着的施襄夏。
“顺儿啊,”小西屏负手望明月,“你说,少爷我这辈子能胜过施襄夏吗?”顺儿看着这个拔高不少的少爷,信心满满道:“少爷必是天下第一,老爷说了,少爷三岁时就能观棋咿呀了,日后必是当世国手!”
小西屏哀哀地看了他一眼,继续对月伤感。
次日,范府人来了家信,小西屏关在房内足足十个时辰没有出门。小襄夏对着空荡荡的棋盘,只能一颗颗摆上古局,将对弈变成了参悟。他时不时捏着棋子出神,错过了午膳,也错过了晚膳,直到月挂斗檐,他才放下最后一子,起身活动了下手脚。
“少爷?”如意站的腿都不会动了,小声唤了句。
“晚膳留了吗?”小襄夏抱歉地看着他,内疚因为自己而累他立了一日。
“留了,留了。”如意忙要跑出去拿饭。
“送去范少爷房里,我陪他一起吃。”
如意撇了撇嘴,还是照着吩咐去了。
小襄夏绕过回廊,走到了紧闭的房门前,略一犹豫才轻叩了下门,里处没有半点声响。他又抬袖叩了两下,才有人打开了门,小西屏吧唧了一下嘴,看着他,两眼饿的直泛绿光:“有饭没有?”
“有。”面前的人暗放下心,隐隐地笑了几声。
“一起吃一起吃,最后一顿了。”小西屏弹了弹早皱成一团的衣裳,转身走了回去。
几碟小菜,可口沁心,吃得小西屏两眼雾蒙蒙。
“施兄啊,”七八岁的模样,却极悲苦地叹了口气,“小弟我家道中落,明日就要卷铺盖走人了,望兄台成就妙手,小弟我日后也好沾沾光。”
他小手颤巍巍颤地捧起杯热茶,心儿却落了地窖。
想他范家乃是围棋世家,怎么也有些个祖上的存银,哎,败家的老爹,真是不知怎么说你好,落得如此地步,难道要七八岁的孩儿给你善后?!
小襄夏替他添了一调羹的豆腐,抿唇想说什么,粉嫩的脸不知怎地褪了些颜色,变得更是玉莹莹了。小西屏是饿的慌了,也没再悲秋感伤,稀里哗啦地扫了大半的菜,才注意到面前的白褂小公子一口没吃,想了想才道:“你吃了才
过来的?”
小襄夏看他眼睛不住瞟着剩下的菜,软软地嗯了声:“你吃吧,我不饿。”
小西屏含着饭,埋头继续吃,当湖书院的先生虽食古不化,这厨子可是一顶一的,好过自家把猪肉做的跟白豆腐似的小厨,想到这儿,不禁想到指不定回家要自己烧水掌勺了,又是双眼雾蒙蒙,将老爹十大酷刑了一遍。
他落了筷,忽然心头堵着什么话似的,将小襄夏的手攥在自己两手中。
心中还不忘颤了颤,小小嫉妒了一番:你说都是日日执黑白子的人,怎地他的手仿若无骨,真比娘亲的手还要细上几分。
“施兄小弟我我”
小襄夏软软地嗯了声,瞧着他。
连平日互不顺眼的如意和顺儿,都有些眼睛里酸涩的,于心不忍。
小西屏本是感怀万千,却不知怎地,话滑到嘴边便成了:“待我二十岁,必会大败天下棋林高手,回来赢你!”
那一年。
当湖书院走了个七八岁的范家小少爷。
那一年。
青梅微酸,竹马正俏,却已是天各一方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卷三:天纵英才
少年英才,老天眷顾。
施家的少爷施襄夏,习棋十余年,却难有建树。而那离开书院的范西屏,13岁便开始展露出出神入化的棋艺,十六岁便已屡胜名家,成为国手。
如今二十岁的国手,重回故里的行程方才定下,就已传的海宁人尽皆知。
那一日,施家少爷在凉亭中,闲闲地独自弈棋。
他穿着淡青色的长衫,眉目清淡的仿佛一笔而就,他的眼黑白分明,永远含着笑。纵亭外热浪滚滚,却毫不为之所动。
“少爷,”如意立在一侧,专心致志为他晃着扇儿,“当年少爷的资质明明在范家小子之上,时隔十二年,他便成了国手,少爷为何不离开当湖,也学他到处与人比试?如意我就不信,我们家少爷会比不上他——”
施襄夏清淡笑著,并未言语。
如意欲言又止,终是作罢,早知这范家小子是少爷的劲敌,当年他就该……就该……在那吃食中加点儿什么……致人痴傻的药。
如意悔不当初时,亭外已行来一列人。
不必细看,单看那陪伴者卑躬屈膝,阿谀奉承的姿态,便知是那位范国手来了。如意本以为他会忘了少爷,径自离去。
却未料,那身着白衣,眉目清丽的少年,就堪堪停在了亭前。
“亭中的……可是……施公子?”
“正是,正是,”那陪伴的人,躬身道,“正是施家的少爷。”
如意轻哼了声,将手中扇儿摇晃的,快要散了架子。
范西屏良久未言,恭恭敬敬地轻拂了衣衫,举步跨入凉亭。
施襄夏仍旧手执白子,凝视棋盘,仿佛这凡尘俗事皆与他无关。直到身后人走近,落座,他方才微微展颜,未抬眼,已出声:“这局棋,是你与程兰如的棋局。”
“正是。”范西屏方才扫了一眼,便已明了。
他少年成名,风华一时无二,朝中官们闲极无趣,便争抢着用银子请来天下强手与范西屏弈棋,以此为乐。
官员的乐趣,也更加为他助长声明。
这一年,先后十数个棋林高手均成为他的手下败将。
“施兄……”范国手,语音发涩。
“范贤弟。”施襄夏微微笑,看他。
“不知施兄可否与小弟对弈……较量?”
他笑,反问范西屏:“为何要较量?”
“施兄少年时便被称为‘海宁神童’,如今学棋已有十数载,却不肯离开海
宁,与高手对弈,如何成的了名?”范西屏单手撑在石桌上,漆黑的眸子,微微上扬着,竟有着稍许的闪灼,“小弟愿与施兄对弈一场——”
“助我扬名?”施襄夏复又垂眼,去细看棋局。
“正是。”
“为何要助我?”
“小弟——”范西屏少年翩翩,不可一世,却独在施家少爷面前,竟不敢多言。
唯恐,言多便是错。
范西屏素手渐握成拳,支吾半晌,终清咳声,掩盖住自己片刻的失神无措:“小弟——”
“无须如此。”施襄夏眉眼带笑,不温不火地打断他。
范西屏未料自己竟被他如此婉拒,复又噎住。
他家道中落,却始终未曾放弃弈棋,大败天下棋手,不过为了能重返海宁时,与心中的“海宁神童”对弈一局。他的用心……这用心……有几多争强好胜,又有几多难以启齿的私心……他自己却不敢深想。
“施兄……小弟我……我……”
施襄夏淡淡地应了声,瞧着他:“你来见我,就是为了十二年前的那句话?想要赢我?”
热辣辣的风,吹在身上,硬是吹出了范西屏一身热汗。
他启口未言,终又作罢。
他名扬天下,却只惦记着海宁这里的施家公子,如何能言?他身负盛名,却甘愿输施襄夏几局,甘愿为垫脚石,如何能言?
亭外的顺儿越发瞧不上自家少爷的模样,隐隐做怒,却未料被如意的扇儿狠狠敲了,抬头望见如意冷冰冰的眼睛,瞬间就如被冰碴子淋了一盆,蔫巴了。
“如意,”施襄夏看范西屏流了些汗,便吩咐道:“拿些凉茶来。”
如意应了一声,快步离开,不一会儿就端了杯茶来。
青瓷的杯,盖拿走了,凉茶上还飘着夏花。
就此一杯,如意可不愿给这位不可一世的范家小子喝什么茶。热死活该。
施襄夏笑著摇了摇头,抿了口,递回给范国手:“喝些吧,免得中暑。”
范西屏双手接过,看着那茶杯半晌,竟不转茶杯,就对着施襄夏饮茶的印子,喝了口。凉茶入口,却压不下这等唇齿相依带来的一股子燥热……
而那石桌上坐着的人,却仍旧清凉神色,看着棋,困在黑白相争之间,眼中再无其它。
那日过后,施襄夏依旧每日在凉亭,自己和自己对弈。
范西屏在海宁整整十五日,却不敢再去见这位少年竹马,觥筹交错的,
奉承赞颂的,歌舞升平的,海宁仍有碧树,仍有棋苑,却再无当年两小无猜的一对小儿郎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卷四:当湖十局
那日过后,范西屏愈发不可一世,与各地高手较量,战无不胜。
渐成“棋圣”。
岁月浮尘,时光荏苒。
十数载的沉淀后,海宁终是迎来了又一当世国手施襄夏。倘若说范西屏以鬼手成名,那施襄夏便是那“落子有仙气,迥非凡手及”。
春兰秋菊,各有胜场。
海宁连出两大国手,却从未真正较量过。不论武林,亦或是棋林,都执著于这“第一手”的称呼,究竟是以鬼手成名的“棋圣”棋高一招,还是落子有仙气的施襄夏道高一筹?
渐成棋林,乃至天下所争执不下的话题。
可偏偏这自幼相识,同乡、同师的国手,从未有过交手的念头。
终有一日,海宁的父母官熬不住朝廷王孙贵胄的折磨,亲自递出请柬,邀二人当湖边,较量一番,也算有个高下之争。
先拿到请柬的范西屏未答复。
民间猜测,许是这棋圣成名太久,怕输,尤其是输给成名比自己晚十数年的旧识。
施襄夏却在接到请柬时,当即应允。
不久,范西屏应邀。
当湖边,独有一亭。亭外十丈远,围着数百人,几十个棋盘。
亭中落了一子,亭外便有人在数十的棋盘上,落上同样的黑白子。
当湖十局,范西屏先手六局,却终打了个平手。
施襄夏眉目含笑,轻将白子收拢:“再来三局如何?”
范西屏看他,恍惚间,只觉这十数年来,他竟未曾老去。仍旧眉目入画,甚至真如传闻所说,不止落子有仙气,人也有着清淡的,远离凡尘的仙气。
反观自己……
范西屏微扬一侧嘴角,甚为自卑,年少成名,浸染棋林,阿谀奉承听了不少,终显俗气了。他微扬的眸子里,满满尽是面前人。
当年碧树下,小小人儿初现眼前,便是如此,压下盛夏浮躁热气。
当年棋苑中,小小人儿月下前来,便是如此,让人心头浮躁难忍。
当年凉亭中,少年如玉淡看棋局,便是如此,让人欲说万语千言。
范西屏不知如何,就应允了他。
心神俱乱下,草草输了三局。
当湖十三局,以他落败为结局。有人在外想要复棋谱,却被施襄夏拒绝了,最后这三局,他并未准人旁观,是输是赢,亭子那一道珠帘隔开了真相。
“十六岁成名,二十岁战无不胜,渐成棋圣,”施襄夏一粒粒拾起黑子
,“我以为你喜好的是世间浮华……”
范西屏未料他如此解读,伸手按在棋盘上,未料却按住了他的手。
依旧仿佛柔软无骨。
范西屏愣了愣,竟不知该说什么,想收回手,却不舍离开。
施襄夏掌心仍旧压了几粒棋,淡淡地笑著,回视他。
“十六岁成名,二十岁战无不胜,渐成棋圣,是为……”范西屏晶亮的眸子里,闪灼着万言千语,他只怕是说破了,便再无相见日,“输给你……”
施襄夏笑起来:“如今你已输了。”
“我心甘情愿,将天下第一手给你,若你……”范西屏竟有些语塞,如少年儿郎对着心爱人,不知如何才能说尽这二十余年的思念,“若你能日日与我弈棋,我便甘愿日日输你。”
“日日弈棋?”施襄夏合起手,缓缓抽出自己的手。
他一寸寸抽出,范西屏的心便一寸寸冰冷。
终归是奢求妄念了。
“倒也不错。”施襄夏,仿佛自言自语。
有风吹进来,隔着珠帘,将范西屏身上的汗吹去。
“你……当真愿意?”
“有何不可?”
“我指的不仅是弈棋……还有……”
“嗯?”
“我并非要把你当女子对待,襄夏……你在我心中……”
“嗯?”
“我在京城二十余年,也曾与一些女子、少年……可我心里……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我……”
“说下去。”
“你我不如就如此过了一生……可好?”
“倒也不错。”
范西屏只觉心头滚烫的,有什么流到身体四肢,甚至眼里滚烫的,热烈的,浓郁的,那些情感,明明如此久远,却从未启齿……未料竟如此简单地,得到了他的应允。
施襄夏继续捡着棋盘的上黑子:“这三局棋谱只你我知晓,可好?”
“听你的,全听你的。”范西屏哪里管什么黑白子的事,他只想着日日与眼前人对弈,管他输赢,只要看他捻棋,时不时瞧自己一眼,便是最好。
施襄夏忽然,微微地,簇了眉。
“怎么?”范西屏已是心头猛跳。
“我听闻委身做女子的……总要适应些时日……”
范西屏长吁出口气:“这……我也不知,可我舍不得你……不如,我来……”
“你可受的住?”
“我?为你,有何受不住……”
“那便好。”施襄夏清淡
笑著,忍俊不禁,终是笑出了声。
范西屏这才恍然,自己应允了什么……
施襄夏抬眸,看了他一眼:“喝口凉茶,免得中暑。”
纵你山水闲走,纵你棋林称圣。
却终究抵不过黑白子间,
那一双眸,那一杯茶。
作者有话要说:哎呦。。自己萌了,满地打滚。可怜的受受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