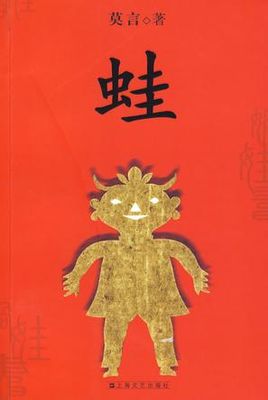屠龙 云荒系列
2016-06-07 阅读 : 次
“想看屠龙?上头早有规定的呀。这是不传秘籍,禁止带游客去观摩的。我也做不了主的啊。”
退休的船司笑呵呵地搓着手。他背后,炉子里星星的微火一明一灭,吞吐着些些暖意。这才刚刚入冬,云荒大陆南岸的这座沿海城市,并不是特别的冷。不过老船司的年纪已经很大了,早早就在屋子里生起了炉子,在椅子垫上毛皮。没有人来访的时候,就坐在炉边读读古书,烘烘手。炉子上炖着晚餐的汤,浓浓的酱汁咕噜咕噜地翻滚着,吞吐着独特的食物芳香。
这温暖的香味,弄得狸猫儿焦灼不安,使劲儿地挠着苏眠的胳膊。苏眠也觉得有点饿了。不过,眼下的当务之急,还是说服船司。看上去,这个老人的确和蔼可亲,但他是不是真的像传闻中那么好说话呢?
“再说,屠龙户也不容易,这可是家传饭碗哟,怎么会愿意给人知道。”
“可是,”苏眠摆出一脸失望的样子,眨了眨眼睛,叹息道,“我千里迢迢地从帝都慕名而来,就是为了一睹屠龙绝技。谁知水漫坪这个地方又很不容易找得到。我这一路上颠倒了三四天,都不曾投对门路。终于有人告诉我,只有来向您恳求,才能觅得机会,亲眼目睹屠龙这门绝技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船司点点头,似有所动,又放低了声音道,“不过啊,实话跟你讲,禁令主要是为了安全。以前没下禁令的时候,有屠龙户在人前炫技,结果呢——第二天,混入城里的鲛人就给他来了个满门屠杀。”
“老先生,我并不是鲛人啊。”苏眠说,“我也不喜欢鲛人。”
“我知道你不是。”老船司有些好笑地说,“看你的样子,是从帝都出来游玩的官家大小姐吧,以为什么东西都新奇有趣。我告诉你,屠龙可不是给小姑娘看着开心的事情啊。”
苏眠微笑:“您可猜错了,我不是什么官家大小姐呢。之所以对这种技艺特别有兴趣,因为我是个医士。”
“女医士?少见,少见哪。”老船司有些意外了。
“敝姓苏,叫苏眠。曾经在迦蓝宫中供职,是侍奉公主的女医官,这里还有帝都太医局的证明。”苏眠抱了抱怀里的狸猫儿,并抽出一张黄黄的纸片儿。
“太医局的人啊,”老船司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。那张来自帝都的信函,把他的一脸的舒适都给刮掉了。太医局未必那么有势力,但在水漫坪小地方,这块牌子还是有作用的。“早先就有太医局的人过问屠龙的事情……”
“您就帮个忙吧。”
老船司低头想了想,说,“我就带你去吧,不过,你可不能说出去。另外,屠龙户那边……”
“我会给他们些辛苦钱的。”苏眠笑道。
“不不,那倒是不能。”
黄昏时分,海上的天空是鲑鱼肚子的橙红色。
屠龙户们都住在水漫坪海岸的悬崖顶上,他们的工场——凌房也在那里。那个地方寸草不生,光秃秃的玄武岩巍然高耸,像一只伸出的手臂,正指着南方碧落海的方向。顶端的城堡经过长年累月风化,和山石融为狰狞的一体。四周都是绝壁深崖,只有一条小道通往凌房。而苏眠就正走在这条道路上。
老船司告诉她,水漫坪的屠龙户,是一家子十口人,其中能操刀的有祖孙四个。在云荒大陆南部海岸各个主要港口,都有屠龙户存在。在有的港口,还不止一家屠龙户。水漫坪这家人,人数不算多,规模也不大,却是整个云荒最出名的。因为这家的祖父曾经亲上帝都,为景术帝表演过屠龙技。不过如今祖父年纪大了,很少亲自操刀,都是两个儿子在工作。长子有一个儿子,也已经出师。今天老大出门了,能够看到的是他家老二,叫支离益。
城门下面,老船司拉开嗓门喊了几声阿益,吊桥就慢慢放了下来。吊桥是原木扎成的,苏眠走在上面,觉得脚底湿乎乎松松软的。这木头像是吸饱了海水,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气。进去以后就是一条上升的甬道,并不深,四壁都是湿漉漉的,粉刷的灰土早就被潮气侵蚀殆尽,裸出横七竖八的岩石。老船司不时地回过头来,提醒苏眠看着路。
这里实在是很破旧,苏眠心想。
按常理想,屠龙户们应该收入颇丰。如果没有一代代屠龙户们的工作,那么云荒大陆上一道黄金命脉就断掉了。如老船司所说,这都是家族的不传之秘,只有他们懂得怎么做。屠龙虽然不存在任何风险,却是一项非常复杂技术,屠龙户家里的男孩子,都要花费童年的三分之二时间来学习这门技艺,才能够算得刚刚入门。而具体步骤中又有很多细节,需要毕生的历练体会,方可臻于化境。所以,连帝都最出色的医士,都会艳羡屠龙户的精湛手艺。
可事实上,屠龙户们无一不是过着贫困而单调的生活。毕生生活在这些个海滨城堡里面,年复一年做着同样的工作,收入仅供糊口。这破城堡也并不属于他们,而是国家提供的。
走到尽头就是大厅了。所谓的大厅,倒是大得出奇。房间里的腥味更加浓烈。一小窗开在离地丈高的地方,露出几星吝啬的晚霞。房间的四壁都淹没在了黑暗中。大厅正中有一个轮廓僵硬的人影。走进一点以后,那人影就向他们慢慢移过来,略微颤了颤,算是向两位客人行了个礼。
老船司拉着这个叫做支离益的屠龙手,说了几句话。那人一声不吭。苏眠担忧他会拒绝,他却回过头来看了苏眠一眼。他的眼神和脸一样,平静得没有任何内容,如同这些岩石的一个部分。
苏眠的想像中,屠龙户这样的人,大抵是形貌粗陋的。这个支离益却说不上难看,轮廓甚至还有些清秀。只是那种平静得近乎麻木的表情,令人心生厌恶,而剃得干干净净的光头,更加重了某种邪恶的印象。
轻微地颤了颤脖子,就算是同意了。
苏眠竟然舒了一口气。
支离益点起了灯。那灯光也是污浊如死水的。在灯火的跃动中,苏眠看见了地上一摊摊红的绿的陈年旧迹,形貌甚是可疑。顺着那些旧迹望过去,她注意到了大厅的墙角有一整圈的水沟,令人作呕的腥气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。水沟里浸着一排大铁笼子,粗重的铁链在水光下泛着金属的污光。支离益一手端着灯,一手就往笼子掏。过了一会儿,拖出了一把长长的碧蓝色毛发,跟着就有一道雪白鳞光,闪现在灯下。
苏眠知道,这就是今晚的观赏物——鲛人。
这个鲛人还小,身体纤细得如同一片银白色的水草。她紧闭了眼睛,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脸庞看上去很美,鱼尾是温润细致的玉色,展开来像一只爱娇的蝴蝶,拖过砂砾地上,留下淡红的一道水痕。
支离益拖着她的长发,一径往内室走去。
鲛人低声的叫唤着。用的是海洋的语言,也不知在叫唤什么。一双只属于他们族类的美丽眼睛,瞪着碧幽幽的绿色。这眼睛,剜出来就是胜过任何水晶宝石的无价之宝——碧凝珠。
老船司和苏眠立刻跟了过去。那就是切割鲛人的地方——凌房。
凌房倒是意外的干净整洁。四壁一圈儿明灯,把屋子照得如同雪洞一般。当中一座石台子,磨得水光铮亮的,拖进来的鲛人,就被拍到了台子上,仰面朝上,蓝色的长发依旧拖到地上。室内先已经有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,在一边儿清点刀具。此时正把一排擦干净的刀摆在一辆车上,推到了石台子边。
这少年也有一张花岗石的脸,酷似支离益。并且,也剃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光头,大约这是屠龙户的规矩吧。
老船司说,这孩子是长子的儿子,这家屠龙户的第三代,今晚给叔叔打下手。叔侄两人都是一声不吭,配合得十分默契。一忽儿就把鲛人捆绑结实了。叔叔转身去洗手,少年则找来一条长布,把鲛人的长发拾起来擦干包裹好,动作流畅得像一个熟练的梳头工。
支离益拿着一支笔,盯着鲛人的腰部打量一番,迅速地目测出皮肤切口,然后画下了几道线条。
笔尖触及皮肤时,鲛人剧烈地战栗起来,像是已经预感到了利器切割皮肤的疼痛。等支离益接连把三瓶烈酒浇到她身上之后,她就不动了。
老船司低声说,这烈酒有双重作用,一来是为了洁净消毒,二来也是要让鲛人在冲天酒气里晕厥过去,一会儿下刀子时就不乱动了。而那个少年包裹鲛人的头发,除了干净以外,也是因为这个鲛人的头发很好看,能多卖好几个钱,需要好好保护。
说话间,支离益已经伏在了鲛人的身边,执刀如笔,轻描淡画,从胸骨下经肚脐,直至下腹部与鱼尾交接之处,割出了笔直的一道。银白色的皮肤沿刀口翻起,一粒粒珊瑚色的血珠子迸了出来,沿着刀锋雀跃,仿佛在炫耀自己的纯洁。
改造鲛人的手术由来已久。三千多年前,毗陵王朝的星尊帝灭海国,将俘虏以为奴。那时候,为了让这些“水生动物”更好地适应陆上生活,为空桑人效劳,星尊帝令号称智囊的大臣苏飞廉研制一种方法,要让鲛人的鱼尾变成两条如人类的腿。苏飞廉试验了一百多个鲛人,才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手术,造出了形容姣好、可以用修长的双腿舞蹈的鲛人,用于贵族们赏玩。后来,所有被捕获上陆的鲛人,都是要把尾巴劈做两条腿的,如此才卖得出价钱。千百年来,云荒大陆上的王朝换了一个又一个,但鲛人奴隶贸易一直都是蒸蒸日上。而做劈尾手术的,也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行业,世代传承。“屠龙”这种说法,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,但应该不如何久远。大约出自某个空桑族文士之口,觉得劈尾一词不够典雅,于是援引中州的古籍,叫做“屠龙”。龙是鲛族的守护神和图腾,鲛人亦自诩他们在海中逍遥游曳的姿态为游龙。而屠龙,屠龙……对于鲛人来说,劈开鱼尾变成人,虽不至死,甚至仍可潜泳,但已经等同于剥夺了作为鲛人的最大尊严,或者还不如被屠杀掉呢。
苏眠瞪大了眼睛,等着看支离益如何完成这“屠龙”的绝技。
支离益动作极快。一只亮闪闪的光头定在那里,几乎纹丝不动。只有手中一把银色的小刀舞成一团光。鲛人腹部皮上的切口还未来得及涌出大量的血,皮肤下的脂肪、筋膜和肌肉就已经跟着分开了。转眼间鲛人的下腹部已经破开一条长长的竖口子,露出腹中肚肠。支离益拿起一根洁白的骨头——或者是鲛人骨,撑在豁口两边,并且让少年把持住,好让他认真探究肚子里的东西。
少年憋红了脸。鲛人腹部的肌肉很紧,他得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撑开。
肚肠是柔嫩的粉红色,在灯光下泛着莹润的珠光。被切开的肚皮还在不停的流血。除了要拉开切口,少年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用一块棉布压住创面,吸血。棉布一会儿就浸透了,于是就换一块。虽然是小事,可是如果大量的血流到肚子里,支离益就无法看清他要做的东西了。少年知道这一点,做很认真,甚至可说是很小心。身边放了很多棉布,那些棉布是反复使用的,已经用过相当长时间,变成一种难以言说的黑色了。
支离益飞快地拉出鲛人的肠子,挑到一边。空出的腹腔露出了后壁,是一根细长的脊椎骨,旁边两只淡褐色的肾脏。
“从腹腔里看,鲛人的身体和人还是很相似的。”苏眠说。
“是啊,”老船司说,“毕竟都是人嘛。”
苏眠有些不以为然:“但是,据说鲛人的胸腔就不同了。他们的心脏位于正中,所以胸腔里面所有的结构都是左右对称的。从这点来看,它们又和鱼没有什么两样。”
“那是为了在水中保持平衡吧。”老船司说。
“假如能看看鲛人的胸腔就好了。”苏眠说,“不过,大概不可能看到吧。剖开了胸腔,鲛人多半就活不成了。”
事实上,苏眠从血液里厌恶鲛人这种生物。根据古老年代的传说,她的祖先来自天上一个名叫“云浮”的美丽国度。但那个国度却被鲛人们灭亡了,幸存下来的遗族为了活命,失去了重归天界的能力,成为大地上永远的流亡者。鲛族,这种来碧落海深处的生物,有着绝美的容貌和冰冷的肌肤,神情仿佛最无辜的婴孩。每当苏眠看见他们,总会感到不寒而栗,仿佛在春日的和煦日光中,忽然被狠狠冰了一下。
在帝都迦蓝,鲛人作为身价最为昂贵的奴隶,被权贵和巨贾们购买收藏,作为玩赏和享乐的对象。贵人家的鲛人,往往和主人之间有着淫乱关系。那些最为荒唐艳冶的传闻有关,无不有鲛人掺杂其中。比如景术帝的宠佞雍容,又比如太医斯悒家的那个女人,雪鱼。这也是人们蔑视他们的原因之一。
“其实要看很容易啊。”老船司说。
“呃?”
“鲛人的胸腔啊,我就经常能看见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,这里的人鱼是经常死的。死了就能剖开来看看了。”
“……为什么会经常死?”
“因为屠龙术,想想也是对人鱼的损伤是很大。”老船司说,“这么多年也没找到一个好的止血药方,很多人鱼都会死于失血过多而送命。一方面呢,就要求屠龙户的动作越快越好,这样少流点血。另一方面,鲛人也最好是年幼点的。那些年纪大了、已经变了身的鲛人。他们的下身已经发育出雌雄区别。手术中除了去掉尾巴之外,还要改造内部器官。手术要拖一个多时辰。除了少数血气旺盛的鲛人,大部分都当场死在那张台子上了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然后,屠龙户就会把鲛人的胸腔打也开来,彻底肢解。你知道,鲛人皮,鲛人的鳃,鲛人的心脏,都是很值钱的,一件都不能落下。这时你就看看它的心脏是不是在正中间。以前领来的游客,碰见鲛人死了的,倒多半很高兴,这样就能看个究竟。”
“……那倒也是,死了就能看了。”苏眠说,“不过我是想问,鲛人死了,屠龙户不用负责任么?”
“不用,”老船司笑了,“鲛人死了就算了。”
“算了?可是,鲛人是很名贵的啊。在帝都,一个健康美貌的鲛人,可以买到上万金铢。相当于一户小康人家几百年的收入啊。死一个鲛人,损失太大了。这些人贩子肯善罢甘休么?”
“那倒不至于。谁都知道,这本来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事情。死了鲛人,主人也都能通情达理,不会太计较的。”老船司说,“说到底……这本来就是不用本钱的买卖啊。”
“不用本钱?”
“是的。这里的主人,不是正经人贩子,而是下碧落海捕捉鲛人的渔家。因为没有做过手术的鲛人,在陆地上活不长。甩着一条尾巴,动不了。只能泡在一桶一桶的海水里。所以,渔家捉上来鲛人,就直接送到海边的屠龙户这里来,做完手术再领回去。伤口养好了,能用新腿走路了,渔家就牵到县府去出售。那里有专门的鲛人贩子,开了店收购。视年龄雌雄,一个鲛人的收购价大概是四五十个银毫子吧。对于这些穷苦的渔家来说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,相当于一年打鱼所得。如果是沧月螺或者端鱼,他们要打上十几二十船,才能挣回这么多呢。所以,只要有一个鲛人活下来,他们就心满意足了。活不下来,他们也不会太计较。”
“心满意足?”
“是啊,这些船家,都是些老实的穷人。鲛人对于他们来说,是海神给的意外恩赐。我在这一带做船司,管理渔船。但凡有渔家捕到鲛人卖回了钱,都会祭神祭祖,还要请同村大吃一顿,叫谢海酒。从中午吃到晚上,村人还要唱歌跳舞点篝火。这种谢海酒,我一年也能喝个十几回呢。这两天村子里也该有的,回头我带你去吃。”
“多谢。我想,那一定是很有趣的民俗啦。”
“是啊,也是本地的一大特色。”老船司颇为自豪。
“您说鲛人的收购价,是四五十的银毫子?”
“是的,不多啊。据说这里的鲛人贩子收了去,运到首府去,卖给鲛人教养所,价钱要翻上几十倍?”
“嗯。据我所知,从教养所里出来,价钱又要翻倍。这时又有一层人贩子在收购,少数资质很差的直接卖为苦力,多数卖给各种各样的伎馆,继续调教。之后层层装裹,层层倒卖,弄到帝都贵族家里的鲛人,就变成天价的了。”
“唉,”老船司叹了口气,“冒着生命危险下海的人,得到的只是零头。钱都叫那些中间商赚去了。”
“岂止是鲛人买卖。其实无论什么生意,都是这样的。”苏眠说。
“那些商人最可恨。”老船司说。
苏眠笑了笑。
“真是的,”老船司说,“偶尔也有人贩子卖了带尾的鲛人,送过来手术。这时屠龙户就要分外小心,商人不好缠。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花了钱,就对屠龙户提出各种要求,不小心鲛人死了,他们也会大发脾气。这时候我就得出面摆平。”
“他们会拒绝向屠龙户支付佣金?”苏眠猜测,“那么,这些难缠的商人,屠龙户也可以一开始就拒绝接他们的活儿嘛。”
“那可不成。”老船司说,“按照规定,屠龙户不能拒绝任何活儿。而且,从来也没有人向他们付佣金。他们的口粮是官家给的。”
“为什么会有这种规定?”苏眠愕然。屠龙户身怀密不外传的绝技,照理说也该有很多丰厚的收益以及挑挑拣拣的特权,为什么——她想问的是,他们会接受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呢。
“自来就是如此啊。”老船司说。
两人兀自闲扯。不知不觉间,支离益已经进入手术的关键步骤了。他的侄儿绷着一张流汗的脸,凑近了去。因为这是学习重要技术的机会,不知不觉得显出一点难得的兴奋来,一双不甚有神的眼睛闪啊闪的。
苏眠深知,屠龙户不愿外人看到手术关键的细节,所以依旧站在五步开外。
因为吸入了大量的酒,那个年幼的鲛人仍旧昏迷着。白皙的脸因为严重失血而显得更加白皙。细巧的下颏,楞楞地仰着——这下颏苍白光亮,像是指向天空的一把利器。
真是漂亮的孩子,倘若能活下来,卖到帝都,一定不止一万金铢的价钱。
有着花岗岩面孔的屠龙户,正在全神贯注地操作。鲛人腹腔已经完全撑开,腹腔下面的盆腔也空了,亮出侧壁。支离益用刀柄分开盆腔后的一条条肌肉,一边分,一边用力压住伤口给鲛人止血。最后,盆腔的一侧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。
根据以前看到的图谱,苏眠知道,这是鲛人的腹鳍鳍骨。
鲛人的腹鳍鳍骨,相当于人的腿骨。无论是腹鳍鳍骨还是腿骨,都是通过下肢的肢带骨和脊柱骨相连接。只不过,鲛人在水中游泳,腹鳍骨不需要承担身体的重量,因而连同肢带骨都长得十分细弱,和脊柱若即若离。这个手术,就是要把这细弱的肢带骨重新连接到脊柱上,做出和人类同样的下肢结构。并且辅以促进骨骼生长的药物,加上强行训练,使得鲛人的腹鳍生长成为可以行走、可以舞蹈的人类的腿。
支离益的技术很熟练。他捉住肢带骨的游离端,用刀削了几下,如同削一只木薯。转眼,那根骨头就切割成了关节面的样子。然后,支离益再用磨刀石把切面磨光。骨头含血丰富,打磨过程中,切面上不停的涌出鲜血。小侄儿递过一罐骨胶,支离益一边磨,一边飞速地用手指挖了一大把,抹在渗血的骨面上。
不一会儿,血就止住了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苏眠说,“说鲛人上岸,尾巴变成腿,叫做劈尾。一般人只想象是把那条鱼尾巴从中间劈开,一分为二。我就一直疑惑,脊柱骨的结构如竹节,不可能变成两根腿骨的。原来真正的手术,却是把与人类下肢相似的腹鳍改造为下肢。看来劈尾一说,是外行人想当然的误传啦。”
“也不尽然是误传。”老船司低声说。
年幼鲛人的骨骼实在太细。支离益朝少年做了个手势,少年跑开了。过了一会儿,拖过来一个大箱子,并且打开。
苏眠看见,箱子里全是白花花的骨头。
支离益弓着背,在箱子里翻了一阵子,摸出来一根长骨,用染血的纱布擦拭一番,然后放到鲛人的身上。比划了几下,似乎不满意,放到一边,又摸了一根出来比。
这些骨头,大概就是以前死在这张台子上的鲛人的遗骨吧。苏眠想。
一连比了三根,支离益才找到了合适的长骨,和鲛人本身的肢带骨并排放好,并且用骨钉钉在了一起。
这样做,无疑是为了加固肢带骨,以防鲛人刚刚站起来的时候,因为不堪负重而骨折。
“可是,这个鲛人还小,它自己的骨头将来还会生长的。”苏眠有些疑惑,“这样给它钉死了,岂不是……”
“等他长大了以后,再做一次手术,把骨撑取下来就是了。”老船司解释道。
“还要再做一次手术么?”
“是啊。即使改造的时候没有加入骨撑,大部分鲛人也都是还要再做一次大手术的。”
的确是如此,苏眠想起来,在帝都看到的很多鲛人,身体都经过一些改造。从最微不足道的纹身,到最惊悚的“千手观音”。这都是商人们为了满足不同买主的特殊癖好,而请某些黑市医士动手术做成的。
支离益的动作的确很快。才一会儿功夫,另一侧的肢带骨也改造、加固好了。他用力一拉,把肢带骨连在脊柱上,连着的腹鳍也狠狠地缩了进来。苏眠盯着看,那只细弱的腹鳍在无意识中猛烈地颤抖着。
少年捧来一罐子药水。支离益用纱布蘸着,涂抹在肢带骨和腹鳍骨上。这应该就是特别研制的,促进鲛人骨骼生长的药物了。
药水有着很强的刺激性。刚刚涂上去,鲛人的腹鳍就由颤抖变成了抽搐,并且越抽越猛烈,腹部一起一伏,鱼尾也跟着甩来甩去,拍得“啪啪”作响,连地上的血水都被拍打起来,形成淡红的雾。
支离益显然很习惯这种反应了,并不顾及鲛人的躁动,用飞快的手法把腹中的所有出血口都缝扎好,冲洗干净。然后内脏回复原位,关好肚子,缝上皮。
“这只是其中一种药,”老船司说,“手术完了以后,还要给他们灌下其他的药水。这些药很神的,能让两条腿在半年之内长到正常人的长度。不过,也都是很毒的药。手术没死,事后吃这些药吃死的鲛人,也不在少数。”
“据我所知,没有哪一种药是对任何人都有效的。这些个药物,对所有鲛人都有效吗?”苏眠发出医士的质疑,“有没有鲛人吃了这个药,没有中毒,却也长不成人腿的?应该有吧。”
“当然有了,白白动了手术,剩下的腹鳍却没能成功长成人腿。那样的鲛人也就算废品了。就像一个没有腿的人,完全丧失劳动力,做普通奴仆都不成。轮到人贩子手里,多半就这样被抛弃了吧。这种鲛人也不在少数。”
“哦,我想……”苏眠若有所思道,“在帝都,每看见一个昂贵的鲛人,他的背后都有无数同族的死尸吧。”
“不错。”
现在,这小鲛人看起来完好无损,只是肚子上多了一道蜈蚣般的缝线口。缝线口抹上特殊药膏,保证她将来不会留下让主顾觉得不雅的疤痕。
腹鳍还在抽搐。支离益一手捉住这新生成的“腿”,一手接过少年递来的剃刀,飞快地刮去了上面的鳞片,露出淡蓝色的皮肤。
刮好了一边,又去刮另一边。
蓝皮肤刚刚露出来时,泛着月光一样的银彩,转瞬间就变得污浊沉暗了。就像刚刚出土的古董接触到空气一样。不过这倒不是空气的作用。仔细看去,原来鳞片的根部受了伤,都在暗暗地渗血。
血不多,颜色很暗。这些伤痕织成网状,如同白色戈壁上龟裂的沟壑。微细的血流在这些沟壑中缓缓流动,渐渐汇聚到下垂的鳍尖,形成一个褐色的血滴子,坠着。黏度极大,所以久久地坠着,拉长。最后终于承受不了这重,轻轻一颤,堕在岩石地板上,摔得粉碎。
终于刮干净了。屠龙户支离益,直起了腰,退开两步。岩石般的脸仍然毫无表情。
这时上来的是侄儿。这少年吃力地抱起一大缸子烈酒,往鲛人的下身一泼。浓烈刺鼻的酒气,再次弥漫在凌房里面。
“这就完了吧?”苏眠问。
“嗯……”老船司说,“一般的客人,只看到这里。”
“呃?”
“一般的客人,看到这里,多半已经觉得很恶心了。我就带他们离开。”老船司解释着,“不过我看你没什么反应啊。因为是个医士的缘故吧?”
苏眠不置可否:“后面还要做什么?”
“其实后面才是最关键的一步啦。”老船司说。
“是什么呢?”
老船司却故意转了话题,买了个关子:“说起来蛮可惜,你注意到没?这个小鲛人还没变身。”
“是啊。”苏眠点点头,“所以不用费时间给它做调整器官的手术。这样,它很可能就不会死在台上了。我可看不到心脏了。”
“嗯,”老船司说,“对游客来讲,是有点遗憾罗。不过对屠龙户来说,鲛人最好还是不要死。只是到这时,鲛人能不能挺过这个手术,还在未知。最后一步,才是对它最大的考验哪。”
说话间,少年已经把放置手术刀具的小车推到了一边,扛过来一把长刀。那长刀比他本人还要高个一点。他把刀背靠在肩上,小心地扶稳了。用烈酒蘸上纱布,拭了又拭。刀锋在他的精心擦拭下显出一丝丝的蓝光,映得少年的眼睛,也发出幽幽的光芒来。
某一刻,苏眠和他对视了一下,发现少年平静的眼底,溢出一丝丝令人惊奇的喜悦感。
支离益蹲在墙边休息,双臂交叠胸前,两只空洞的眼睛木木地瞪着,似乎在养精蓄锐。
“这也是对屠龙户最大的考验。”老船司似乎忍不住兴奋地说,“前面再怎么麻烦步骤,都是小菜一碟。要极快,要极稳,要极准。一瞬间就可以完成的这一步,其实凝结了屠龙中的最顶尖的技术。可以说,屠龙户一生的修炼,其实就在这一刀……”
突然,雪光,刺目一闪。
就像一颗极亮的流星,骤然划过长夜的天空。真的,苏眠明明连眼珠子都不曾离开过那张石台,却什么都没看见,没有捕捉到。
还是明亮的凌房,还是泛着淡红血光的空气。屠龙户支离益,仍旧靠在墙边,脸如苍岩,两手低垂,没有任何情绪改变。
老船司还在身边,絮絮叨叨说着什么。
然而,视野里面,终究还是有什么东西,刺激着已经钝化的视觉。它在闪烁着,突兀着。于夜的宁静表象之后,顶出一道喑哑的疯狂。
那是一条鱼尾,长在小美人鱼身上,有着优美纤细弧线的银白色鱼尾。
这条鱼尾已经离开了鲛人的身体,它还没有死去。凭着一点点动物的本能,在沙砾的里面上拼命翻腾,一次又一次地从地面上弹起,就像一个重伤垂死的人,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求救。
断面上流出的血,洒了一地,像盛开的珊瑚。
最后弹跳不起来了,却还不甘心,在地面上扭动,一直滚到墙角才停下来。
一路划出血痕,好像一纸浓墨重彩的文书。
苏眠好不容易才把视线从那只砍下的鱼尾上挪开。再看那台子边上,鲛人的身体只剩了一半。
断端面上,愈伤用的药膏已经涂抹好。因为刀够快,甚至没来得及流太多的血。那个少年手持纱布给它包扎。怕出血,一边包,一边用足了全身力气死命压紧,把鲛人的下身包得宛如一只粽子。
那把一人高的长刀,居然也没有沾上一滴血。真是快到了极致。(这明显还是武侠桥段啊。)
苏眠忽然明白过来,所谓“劈尾”一说,是绝对真实的。而且,不是妥协地一分为二,而是把代表着海洋生命的鱼尾,给完完全全的劈下来!
躺在砧板上的、这个尚且年幼的鲛人……刚才,她——觉得痛吗?
苏眠和老船司都没有听见鲛人的叫喊。鲛人早已深度麻醉了,她的上半段身体也不曾挣扎,是应该不痛的。
她的视线慢慢的挪了上去。
看见了张开的嘴。小鲛人依旧紧闭了双眼,修长的睫毛覆盖了她的沉睡。可是珊瑚色的嘴唇,不知何时张开了,撑成一个完美的圆。
又如同一个深沉无底的洞窟。
那一刻,苏眠仿佛听见了一阵宏大的嘶喊,从遥远的深海抑或苍穹喷涌而出。
似乎过了很久,苏眠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:“她死了?”
“没有,”老船司轻快地说,“砍得很准,很好。她没死,不会死的。”
“哦……”
“不错,不错,今天真不错。你看出什么门道了吗?”
“太玄了,怎么看得出?”苏眠干笑了一下。
“呵呵,外行人自然是看不出的,”老船司眯着眼睛说,“我也是看了许多回,才知各中奥妙。”
“愿闻其详。”
“说来也简单。第一是位置要准,劈得位置高了,把身体部分也伤了,甚至穿透腹腔,则鲛人必死无疑;劈得低了,或者砍得歪了,剩下一截子尾巴杵着,没有那个买主看得过眼,若说补砍也没有哪个鲛人受得了第二刀。手要稳重有力,这么粗的鱼尾,里面又有一根刚劲的脊柱骨,务必要一刀劈断。不仅要一刀砍断,还要越快越好。这么大的创口,要立刻堵住。慢了的话,鲛人会生生的失血而亡。”
“真是不易。练成这身手,就是去做剑客也绰绰有余了。”苏眠评价道。
“呵呵,他们是屠龙户,做不了剑客的。”
苏眠掉过头,去看那两个屠龙户。支离益蹲在墙边休息。那一刀果然用去了很多力气,他仿佛在喘气。不过连喘气,这个沉默的屠龙户也不曾发出一点点声音。而那个少年则忙不迭的拾起支离益放下的刀,洗洗擦擦。刀要尽快擦拭干净,血沾污的时间一长,就没那么锋利了。
这时候,支离益忽然站了起来,走到墙边,拾起鱼尾,用纱布包好,装在一个袋子里,交给了老船司。这似乎是一个仪式,表明屠龙户完成了一次工作,向村人交代成果。
而那个少年抱起包裹好的鲛人,送到了另一个房间去。也许是鲛人比较重,也许是站立时间太长,双腿不支,苏眠发现他走路有一点步履蹒跚。
小鲛人的头巾散开来了。海藻一样的蓝色长发拖到地方,沾上了它自己的血。
那里面大约是一个药房,在那里,她应该会被喂下很多药物。或者,她能够顺利长成一双人类的腿;或者,她会死于药物中毒;又或者,她什么也长不出来,成为失败的废物。
长成人腿的她,还会经历无穷无尽的贩卖、训练和改造,最后成为一个又一个帝都贵族用于发泄的玩物。鲛人命长,她至少还有两百年可活,直到年老色衰无可玩赏,被杀死。只留下一对名贵的眼珠,成为贵妇的宝石。
劈去鱼尾,只是这漫长历程的第一步。
苏眠觉得疲倦了,向老船司示意,想要离去。老船司朝支离益使了个眼色,支离益领着他们,回到一开始的那间大厅。天早已全黑,这一回,他点亮了一盏较大的灯。亮光之下,这间屋子显得十分破败,但却也不那么阴森了,只是普普通通一间穷人家的客厅而已。
苏眠急欲离开,却被老船司拉住了,要她在一张凳子上坐下。
“他家老大的老婆煮了粥宵夜,请客人一起吃的。”老船司说,“这是他家历来的习惯,不要拒绝。”
苏眠有些诧异。看看门边地上,果然坐了一个邋遢的妇人,正朝她谦卑地笑。
过了一会儿,那个少年抱着一大罐子粥和一摞碗出来了。那妇人用手撑着地,艰难地挪了过来。少年把一只长柄的木勺递到她手上。她用勺在罐底捞啊捞的,努力地从清水一样的“粥”里面捞出一点稠的来,盛满了一碗,然后小心翼翼地捧给苏眠。她一直坐在地上,那碗粥捧得比她的头顶还要高。苏眠慌忙接过来,注意她那双手因为长期撑地行走,粗糙得像脚底一样。
妇人探着身子,又努力捞了一碗稠粥,捧给老船司。然后才是支离益一家的粥。老船司接过粥来,却端给了那个少年,把少年手中的碗换给了自己。少年咧了咧嘴,露出今晚的第一个笑容。
苏眠低头看看,那粥不知是用多少年的糙木禾米熬成的,清汤寡水还泛着铁锈红色。大家闷头都不说话,闷头喝粥。一夜劳顿似乎对支离益并无半点影响。少年岩石一样的脸上,却已经渗漏出点点倦意。他捧着粥碗咂得山响,很满足的样子。少年一点些微的情绪感染了苏眠,这个夜晚屠戮鲛人的沉暗血色,也渐渐在这合家食粥的温暖气氛中渐渐淡去。苏眠捧起粥碗,决定学老船司,津津有味的喝下去。
忽然,她从碗边上看见一双绿眼睛。
海洋的颜色。
苏眠猛抬头。那双眼睛也在看她,依然是谦卑的微笑。那双眼睛是属于主妇的。苏眠再一看,发现那妇人的脏头巾里,掉出一绺长发——尽管这头发枯涩不堪,可也能看出本来是蓝色的!
“她是——鲛人么?”苏眠猛地放下粥碗,惊呼起来。
“是啊,”老船司头也不抬地说,“她是鲛人。就是那种劈了鱼尾吃了药,却没长出长腿来的鲛人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屠龙户太贫贱,根本讨不到老婆的。”老船司解释着,“所以他们都是捡这些被扔掉了的鲛人——其中有不算太残废,略微能够自理的,拿来做老婆。”
“他们这些人,总有女儿的吧。”
“他们不养女儿,养不起。女儿又不继承手艺,所以生下来就杀掉。等到要传宗接代了,就挑一个在自己手中弄残了的鲛人。所以屠龙户们的老婆是鲛人,他们的妈妈是鲛人,祖母也是鲛人……”
“等等……”苏眠阻住了他。
然而她张着嘴,却是什么也说不出。
她记得清清楚楚,鲛人的遗传是强势的。人类和鲛人的混血后代,都会天生一条触目的鱼尾。也就是说,都算是鲛人。
“是啊,”老船司看出了她的疑惑,接着说,“其实,他们这些人生下来,也是要劈一次尾巴的,一般就由父亲亲自操刀。但是婴儿劈尾之后,更容易死。所以这些屠龙户人家,都是人丁不旺呢。去年支离益就有一个儿子,生下来三个月做劈尾术。可能因为没保护好吧,当时就在这里断了气。”
苏眠没说话,那个鲛人主妇还在朝她微笑。她忽然觉得,无论如何也喝不下手上的这碗粥了。
老船司半开玩笑道:“正是因为他们和鲛人差不多吧,也都受过劈尾术,所以才会个个都是屠龙能手呢?自己对自己的亲族最了解,动起手来会分外麻利些吧?”
鲛人是奴隶,是贱民。屠龙户,也只是另一种贱民,另一种奴隶。他们毕生练就的绝技,用于屠杀同族,并且不能获得任何报酬,不能有任何地位。都是枷锁中的人,彼此之间,世世代代,冷漠无情地、麻木不仁地、自觉自愿地屠杀下去。这才是云荒的规矩。
苏眠放下粥碗,盯着表情木然的屠龙户一家人,盯着支离益,盯着少年,盯着鲛人主妇。她低声然而认真地说:“我给你们钱,你们离开这里,不要再做这种无聊营生了。”
支离益从碗边抬起头,看了苏眠一眼,麻木的脸上并无任何表情。那个妇人却有些惊恐,忙忙地低了头不再看她。
苏眠提高了声音,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。
他们连头也不抬,只是呼噜呼噜喝着水一样的粥。
“回答我!”苏眠厉声说,“——回答我啊!”
“苏医士,你这是干什么。”老船司苦笑着说,“你让他回答你,他怎么回答?”
苏眠错愕。
“他们是哑巴啊。每一个屠龙户,生下来就被灌了哑药。”
“……”怪不得从来没听见他们说话。
“他们是不可能离开这里的。”老船司叹了一声。
苏眠呆了呆。是了,她不该提这样白痴的要求,这太不像她自己了。她挤出一个笑容:“我知道,跟他们开玩笑的嘛。”
从城堡下来,已经是后半夜了。夜风很冷,听不见鸣虫的叫声。老船司邀请苏眠一起回他的小屋,烤烤火等待天亮。
今晚的鲛人尾也抱了回来,郑重地挂在屋檐下。
狸猫儿已经睡着了。苏眠心想,今晚没有带他去看屠龙,真是明智的决定啊。
炉子上熬着的老汤,又冒出了芳香的白烟。老船司的兴致也跟着汤的热度涨了起来,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,一边赞叹着“这可比屠龙户的粥强多了”,一边殷勤邀请苏眠,同来一碗。
“是鲛人肉汤吧?”苏眠问。
“不错,鲛人肉比任何一种鱼肉都鲜美呢。”老船司被汤的热气熏得红光满面,“每次劈下来的鱼尾,都拿来办酒席呢。村里的老人,才能分一点拿回家熬汤喝,非常滋补的。”
“酒席……”苏眠悠悠地问,“是所谓谢海席吗?”
“对啊,本地的风俗。”老船司说,“明天一起来吧,能尝到最美味的鲛人菜呢。”
“不行啊,”苏眠笑道,“我赶时间,明天一早就得走了。”
“那太遗憾了……”老船司一面吹着热汤,一面衷心地叹息着。
苏眠不再应声,也不再做什么。她一心一意等候天亮。窗外,却还是死寂的冷夜。一片漆黑中,只见远处海滩,有光芒隐约起伏。
“大约是渔人们为庆祝捕获鲛人而点燃篝火吧。”苏眠无意识的自语着。那火光开始只是一点两点,后来就连成线,像一个变形的“人”字。再后来愈燃愈盛,一直蔓延到南方碧落海的深远处,融入一片无涯的星海。
(完)
呃,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文会不会觉得很变态。如果有影响大家的食欲,偶道个歉先。其实我特别注意减少了气氛的渲染,有关手术的描写也是简略了的,并且都是按照写实的来,不带任何夸张。如果有学医或者学生物或者帮助妈妈杀过鱼的同学应该看得出来。文章是以一个冷漠的医士(苏眠)的视角来写的。鉴于她的职业以及她的种族对鲛人的仇恨,她一直都冷眼旁观,不认为对鲛人屠戮是残酷的。但是最后,当她发现屠龙户其实也是鲛人后代的时候,这种残酷由生理上的刺激晋级为灭绝人性的阶级压迫。她的立场从此改变了。
PS:当当当,梦旅人系列的女猪正式登场。资料如下:
姓名:苏眠(睡睡醒醒)。年龄:不详。籍贯:云浮岛翼族的后人,即传说中的云之眷族。出生地:云荒,叶城。婚姻:未婚。外貌:中性化的气质美女(也就是说其实并不美女)。职业:学识渊博的旅行者,经常扮演各种职业。特点:抱着一只会变色的狸猫,这一篇我好像都忘了写他。